对比所谓的 GRE, GMAT, 或SAT 的 Quantatitive Test, 中国人大概都好怀念高中的数学题,三角函数,立体几何,多元函数,复数,还有那些一度让我绝望的复杂应用题。这些构成高等数学的基本单元居然能被中国的数学先辈挖掘到如此深度。其思维模式和思维强度即便是他国仰望到颈断也是无法达到的高度。
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美国入学标准化考试的考试语言转换成汉语,那我们会考几分呢?
抱着这种心态,曾经做过实验,我把 GRE verbal 中的 analogue 的最难的15道题目换成汉语,给我尚在读小学的弟弟做,他居然都做对了,完了还骂我一句:你当我白痴么?!
把我给2个不行。一股悲凉之感油然而生,是啊,原来我们都2得厉害!
======
把问题复杂化永远比把问题简单化要简单上千倍,也不负责和自私自利到千倍。
每次看到那种纷繁纠结的所谓完美现代的数据模型和那些抱着无人能懂的高度,向普众开光的模型开发者的笑脸,我总是无奈叹气,心想那些自以为可以 capture reality/truth 的愚人救世主又再度出现。而那些从一开始就说明,我这个 model 只适用于 very limited context,对于这种 model 我都会看的很仔细,甚至试图搞懂模型背后的衍生意义,不是因为 model 主人的谦虚,而是因为他的确是说了实话。因为这种人懂得那些今天开这个玩笑,明天拿那个说教,其实到头来还不是拿自己开涮的粗浅道理。
然而,漠然看着自己的做题笔记,看着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的逻辑思维转换到出题人所谓的标准思路的过程。心中仍然是悲哀的。当雄鹰有心收敛起羽翼,唯恐被篱笆上的荆棘所刺伤。当骏马被惶恐地套上鞍辔,不安地局促于槽厩。于是,那些自以为可以预知天象,预知未来的“大师”每天都在演戏。是的,既然要演戏,那就要对得起观众。
而那些曾经金戈铁马壮怀激烈的武士,如今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天意”的脚下,那令人倍感惶惶不可终日的“天意”,那令人颤栗晕厥的“天意。”
以前,有好友和我说,投行可怕可恨,但也可怜可悲。因为无论他们多么卖力,立下多大的功劳,也只能推迟而无法改变最终身死族灭的命运。
倒不是因为好友发马后炮,而是因为他的确是看到了那个行业的本质。这其实并不是时代和个人的悲剧了。
古有自媚于上的卫青,恂恂然似不能言的李靖,再到后世郁郁而亡的狄青,屈死风波亭的岳飞……
要明哲保身,全始全终,便只能放弃自己的骄傲和个性。因为只有活的最长的人,才能笑的最久。我知道,肯定有人要骂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和我灌输“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气节!!气节!!!!你懂吗?懂吗????正所谓‘打死不吃嗟来之食!!’”
我想我大概是懂的吧,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太懂得人生气节的意义,所以我才会更体恤那些懂得哲保身人的背后故事。“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苟且得去死,而不是苟且得去活,因为生存本身就是伟大的。
=======
那些现在头顶有犄角,满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个性青年,试问他们其中,到了35岁到40岁,在面临中年危机后,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这场终极游戏中,在时间的宿命面前,试问还有多少人还有当初狮子般的雄心和骆驼般的毅力?
年轻时笃信人定胜天,编织谶纬,制造天命,年老时却敬天畏神,虔诚礼佛,这种转变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
也许根本无所谓进步或退步。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从晚清诗人蒋智由的这句诗里,我们可以清晰听到一个民族从历史深处传来的那一声叹息。
=======
对于所有的录取委员会来说,GMAT 只不过是你录取材料中一个数字罢了,仅此而已,你为之耗尽心血拼搏几个月的结晶,最后不过是 AO 花时间看几秒钟的东西——800,750,600,和你大学的 GPA 一样,所有的标准化考试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考察你能否应对各种学院高压学术的尺度之一。所以,我们身边每年都有考了 600 多分或者本科 GPA 没有3.3的人仍然是拿到了 HBS 或者 Stanford 的 offer的牛人,各种缘由只能去问 AO 了。
考得好不代表你会被录取,因为这只不过说明你有资格进入这个竞技场罢了,而考得不好也不说明你就被自动屏蔽,因为录取的过程非常主观,AO也是人,不是机器,看多了眼睛会酸痛,坐久了屁股会麻木,所以如何使你从重围中脱颖而出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你的 essay,因为这是不可能被数字化的东西,也是 AO 区分申请者档次的唯一准则。
不好意思,写完才发现有点逻辑混乱,懒得修改了,又不是在写 essay,洋洋洒洒,写了半个小时。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还在 GMAT 考试中挣扎的各位烤鸭,胡乱码字,顺便给大脑放松下。其实写了这里这么多就让那些没有考好,不敢把自己分数贴出来的人,看看录取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这肯定不是以 GMAT 为中心的一场游戏。
阿弥陀佛,絮叨完毕,继续做题去也。






 发表于 2008-12-29 20:20:00
发表于 2008-12-29 20: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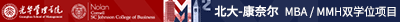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1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13号